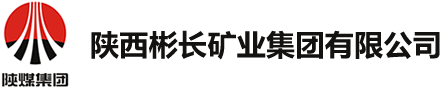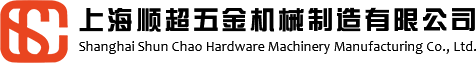文藝生活
東倚太行之巍峨,西臨黃河之滔滔。山西,素有“表里山河”之稱,不僅以遍布全境的古建筑被譽為“地上文物看山西”,更因晉國故地、北朝腹心的歷史淵源,蘊藏著豐富而珍貴的地下遺存。
此前,我已踏足晉南,在這片姬姓晉國發源的土地上尋幽訪古。晉國博物館的陳列與講解,讓我對這段歷史有所認識。
雙節期間,我有幸與父母同行,將探索的足跡向北延伸至太原、大同,對這片與關中一樣承載著厚重歷史的土地,有了更深的認知。
禮樂制度,曾是周王朝政治體系的重要支柱。歷史課本告訴我們,平王東遷后王室衰微、禮崩樂壞。但那終究只是文字的描述,缺乏一種具象的沖擊。

在山西青銅博物館,附耳鳳螭紋蹄足鑊鼎安然沉睡于特制展柜中。這座出土于趙卿墓的青銅鼎,甫一入目,便令人震撼,因為它實在龐大。口徑一米、高逾90厘米,體量龐大,渾厚古樸,是我國目前已知春秋時期最大的鼎。
龐大,只是視覺上的沖擊。展柜一旁,七件紋飾相近的升鼎由大至小整齊排列,秩序井然,流露中和之美。然而,若是讓周禮的追隨者們瞧見了,必然會受到精神上的驚嚇。
趙卿墓的主人趙簡子,作為趙國的奠基人,在彼時當屬卿大夫之列。依《周禮》規定,他只能用五鼎,卻以七鼎隨葬,實為僭越。禮崩樂壞,不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鼎身上的銘刻。而從晉國公室對此無力約束的歷史事實來看,能窺見未來三家分晉的一角——趙、魏、韓、智等卿族,早已尾大不掉。
北魏孝文帝改革,是歷史課本上的另一個知識點。出身于拓跋鮮卑的孝文帝元宏,深受太皇太后馮氏影響,廣泛移風易俗、推行漢化,并將都城從地處邊遠的平城遷移至中原腹地洛陽。
在大同云岡石窟,除卻“雕飾奇偉,冠于一世”的藝術成就外,講解員特別提及了第3窟這個“爛尾工程”:終北魏一代,該石窟的內部工程都未完成,現存佛像實為唐代補雕。其停工之原因,正是遷都。
望著千余年前隨著工程停擺,被工匠隨意棄置的石材,我的思緒不禁飄向更北方。拓跋鮮卑雖起于草原,定居中原后卻難敵新興的柔然。為護衛平城,北魏于邊塞設立懷朔、武川等六個軍鎮。
然而,隨著孝文帝南遷,平城與六鎮成為北魏的另一個“爛尾工程”。昔日“國之肺腑”的邊鎮軍民,轉眼淪為被時代遺棄的群體。短短幾十年后,在不公與動蕩中,他們揭竿而起,為北魏王朝敲響覆滅的鐘聲。
曇曜五窟巨佛高大、莊嚴雄偉;音樂窟形制侈麗、場面恢宏;雙窟彩雕迤邐、連綿華美……宗教雖為虛幻,藝術確為真實。云岡石窟,無疑是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、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。但于我而言,那些或古樸或華麗的造像,終究不及一個“爛尾”石窟所帶來的歷史回響更令人心潮起伏。
記錄在書籍中的歷史知識,與眼前的文物古跡互為印證、彼此詮釋,帶來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。古人云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,大抵便是如此。在求知中行走,在行走中思考——還有什么,比這更值得沉醉呢?(文家坡礦 韓炳萱)
編輯:達文娟